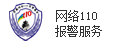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副总裁章俊为《央行观察》撰文指出,要在经济潜在产出水平持续下降的同时,维持中国庞大的日益老龄化人口的消费水平,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将更为巨大。而这又将会直接或者间接的转化为政府债务水平的上升,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这就在实际层面造成了中国未来“未富先老”的严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也是最近政府准备在十三五期间全面放开“二胎”背后的考量,虽然我们认为政策应对到来的时间点本来应该来的更早一点。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季度中国经济数字不尽人意,由于需求疲软和产能过剩的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持续下滑,GDP增速也自2009年一季度以来首次跌破7%。唯一亮点是消费相对平稳且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上升。
前三季度累计增长6.9%,其中消费拉动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出0.2百分点。消费对GDP累计同比贡献率也达到58.4%,显著高于去年同期的51.2%。同时,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同比增速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异常平稳,甚至最近几个月出现小幅反弹(图1)。
官方和市场投资者对“异常坚挺”的消费数据解读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再平衡”,从之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增长的模式开始转向消费。目前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的趋势不改,即便在年末和明年一季度企稳,也很难会看到明显反弹;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造成中国出口复苏依然前景黯淡,更不用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所带来的竞争力下降问题。在此背景下,消费在“稳增长”过程中被寄予更大的期望。
但消费真的能成为解救中国经济的“白衣骑士”吗?
鉴于中国经济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同步降临,虽然短期内向消费转型的势头良好,但我们对中长期内中国消费的可持续性增长有所担忧短期内,投资下降,会造成就业下降,最后会传导到消费。因此在经济下行过程中,消费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独立于经济周期之外的。即便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看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驱动因素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转向消费驱动增长,消费都是有所放缓。
从基本逻辑上来说,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的下降会造成就业率和工资涨幅的下降,之后会在一定时间内传导到消费,从而拖累消费的增长。因此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原则上消费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独立于经济周期之外运行的。即便是从结构角度来看,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转向消费驱动增长,消费在此过程中都是有所放缓。而消费对GDP贡献的上升,往往不是消费增速本身加速的结果,而往往是投资增速下降过快所造成的。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三期叠加”的困境,国内外需求疲软,造成企业库存居高不下和开工率严重不足,其结果必然会对就业造成负面冲击。
而我们之前也反复提到过,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保7%的执着,并不是对某个数字的痴迷,更多的是对就业和其背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担忧。而克强总理也在很多场合强调“只要就业平稳,GDP增速高一点或者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之所以政府对刺激政策的力度一直有所保留,主要还是因为国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就业恶化的问题。即便如此,我们从草根调研数据以及类似采购经理人指数以及央行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等景气指数中的就业分项指数来看,当前就业的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压力,而之后向消费的传导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工业企业利润持续下降对工资增长水平的抑制,以及低通胀造成实际利率高企,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消费造成拖累。3季度居民消费信心指数的下降可能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未来消费增长疲软的先兆。因此我们认为在本轮经济下行周期中,虽然投资和出口疲软消费的拖累效应的显现会有所滞后,但不意味着消费会完全独立于经济周期。
但如果我们跳出周期性的视角转而从结构性视角来看,就业和消费问题可能会有所变化。日韩等经济体转型过程中,人口结构拐点往往滞后经济增长拐点10-15年左右时间。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投资率的下降会对就业造成冲击,这往往是发展服务业在短时间内所不能完全抵消的,因而会进而影响消费增长。而中国目前区别于其他例如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转型经验的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是经济增长拐点叠加人口拐点。
根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2015年中国人口结构中的劳动力占比开始下降(具体表现为抚养比上升), 这就意味着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压力也在下降。因此可以预计只要在转型过程中,投资和出口增速不出现断崖式的下跌,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就会保持大体平衡,甚至是维持供低于求的略微紧张的局面。而这也会带来工资水平的持续平稳增长,这对于向消费转型的经济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
但我们也需要指出的是:人口拐点的过早到来会造成消费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中长期内出现问题。人口拐点到来意味着潜在产出水平的下降,或者通俗而言就是创造财富的能力的下降,而同时人口老龄化造成对国家财富消耗强度不降反升。但为了维持日益庞大的老龄化人群的社会福利水平,相应的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例如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会明显上升。以日本为例,日本的政府债务/GDP比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超过200%),而日本恰恰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但反观日本人口拐点之前,政府债务/GDP比率也就在60%,和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大致相当(中央加地方总债务水平)。
但在人口拐点之后,日本的政府债务水平直线上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支出的飙升。和日本相比,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虽然中国在人口拐点的政府债务水平和日本大致相当,但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却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日本。日本在90年代人口拐点时将近2.8万美元的人均GDP(不考虑价格因素),中国在2015年人口拐点将至之际,人均GDP仅为1万美元左右。
这也就是说,要在经济潜在产出水平持续下降的同时,维持中国庞大的日益老龄化人口的消费水平,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将更为巨大。而这又将会直接或者间接的转化为政府债务水平的上升,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这就在实际层面造成了中国未来“未富先老”的严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也是最近政府准备在十三五期间全面放开“二胎”背后的考量,虽然我们认为政策应对到来的时间点本来应该来的更早一点。